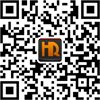如何让员工从工作中获得意义感、满足感和自豪感,是ESG时代人才资源管理的重要议题。人类学家詹姆斯·苏兹曼追溯了从地球上生命的起源到忙碌的现代,畅想智能化的人类未来,重新审视工作之于人存在的意义。[1]
什么是工作
经济学立足于稀缺性,认为努力工作是弥合人类无限的需求与现实世界有限资源的差距。从把工作看成为了谋生的经济问题,那么通过工作,我们获得了以“报酬”、“资源”和“收益”为名的工作所得。
苏兹曼认为从稀缺性问题的谋生解释很难区别工作与休闲。因为工作是“收别人的钱去做一件事”,休闲是“主动付钱去做一件事”,进而工作与休闲可能指向的是同一件事,比如对于古代的猎人而言,猎杀麋鹿是一项维持生存所需的工作,但对于发达国家的猎人而言,则变成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往往非常高。
如果认为工作的起源在于一种基于永恒稀缺性的经济体系,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相比于原始社会,现代人如此忙碌。苏兹曼用30年的时间深入非洲南部的原始部落进行考察,认为是生存的有限需要与无限欲望导致了这一矛盾: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物质欲望却很少,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他们只需要付出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能得到物质满足。
按照苏兹曼的定义,工作是WORK而非JOB,工作不局限于如何谋生,而是“有目的地在一项任务上花费精力或付出努力,以实现某个目标或目的。”
工作的历史变迁
人类与工作的关系经历了从低欲望的原始生活,到田间辛苦劳作,再到向城市迁移的工作,最后立足于智能化的未来。
-
原始社会
原始社会是低欲望的,人类学家以现代狩猎采集部落的追踪调查研究为例,从事狩猎采集的成年人每周觅食时间平均略多于17个小时,能够很容易满足自己的营养需求,从而将大部分时间用于休闲。此外,每周花费约20个小时从事做饭、捡柴火、搭建住所以及制作或维修工具等活动,相比之下现代人每周工作时间是狩猎采集部落的两倍。
“短期”思维是解释狩猎采集原始工作如此“休闲”的原因。在采集狩猎的模式种,人们从劳动中获得直接、即时的回报:吃的食物都是当天弄到的,或在接下来几天里偶尔弄到的。这些食物既不经过精心加工,也不储存起来。
狩猎采集活动是即时回报型的经济形态,狩猎采集者将人际关系视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延伸,大自然同他们分享食物,他们就与别人分享食物。
所有“即时回报型”社会都摒弃了等级制度,遵循“按需共享”的原则,同时也履行分享的义务。食物和物品是根据接受者的索取实现再分配的,而不是根据赠予者的主动奉献进行再分配。因此,在此很少存在勤劳与懒惰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可以容忍的盗窃”。
-
农业社会
向农业转型的一个变化是,工作从“即时回报型”经济模式转向“延迟回报型”经济模式,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以维持下一年的生活。狩猎采集者几乎把所有注意力都集中在当下或不久的未来,而农场上清理土地、犁地、挖掘灌溉沟渠、播种、除草、修剪和培养农作物等几乎每一项任务都是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未来的目标或管理未来的风险。如果一切都做好了,到了收获季节,他们就会有足够的粮食收成,支撑他们度过下一个季节性周期,并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种子储备。
苏兹曼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认为自己通过劳动使土地变得高产,作为交换,土地让他们获得了未来的食物。换言之,农民认为土地欠自己一个收成,实际上是欠了自己的债。更甚者是,农民将自己与土地之间的劳动债务关系扩展到人际关系,他们在直系亲属或核心亲属之间相互分享,但在这个范围之外的分享被界定为一种交换,而且经常是不平等的交换。在农业社会,没有免费的午餐,每个人都要工作。
-
工业社会
工业革命进一步使工作与即时回报脱节,并且刺激着我们对物质的欲望,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几 乎已经消失,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消费构成闭环。对经济增长永无止境的追求,努力工作是满足经济无限增长的唯一办法。
服务业的迅速扩张是大规模工业化的必然结果。另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中涌现出了大量无意义的工作岗位,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为此专门讨论了毫无意义的工作。
当工作不可避免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时,“如果时间充裕,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这也是现在膨胀的官僚机构低效的现象。官僚机构总能产生足够多的内部工作,呈现出忙碌的表象,刻意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以便确保本机构能够持续生存和扩张,但工作效率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
工作与人的关系
在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人们担忧资源稀缺,因而勤奋工作变得重要,人也变得越来越忙碌,但“技术性失业”从未远离。苏兹曼认为,智能化、自动化技术的到来使我们再次处于历史上一个相似的变革时期。如果机器人代替人去做重复性的工作,那么人该做些什么才能更有价值。
苏兹曼提出在描绘人类与工作的关系的历史时,有两条路线是最明显的:
第一条路线描绘了我们与能源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所谓工作,终究是一个能量交换过程,而活的有机体与死的、无生命的物质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做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只有生物有机体才会主动寻找并获取能量来维持生存、生长和繁殖。
第二条路线是人类的进化和文明之旅。沿着这条路线探索下去,就会发现当我们的祖先逐渐掌握不同的技能时,为什么会磨炼出如此强烈的目的性,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建造金字塔、岩壁绘画等活动中找到意义、欢乐和深深的满足感。这条路径还揭示了古人所做的工作以及掌握的技能如何逐步塑造他们感知周围世界以及与周围世界互动的方式。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中,我们强调第一条路线,而将第二条路线作为辅助。自动化有可能彻底改变人与工作的关系,面对智能技术的挑战,重新回到第二条路线,思考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才是重新认识工作的意义,获得工作满足感的正确道路。
参考资料
[英]詹姆斯·苏兹曼:《工作的意义:从史前到未来的人类变革》: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35412857/